早前得到提示:“Don’t make great art. Make it honest.”
這句話一直徘徊於腦海不散。
Honest, 誠實。
對他人不撒謊,不算難。但要對自己完完全全地誠實,何其難。
誠實,需要勇氣,也需視野。誠實地面對自己的不足,發現自己未如所預設地 「強大」、「聰明」、「看得開」、etc etc、之類之類 (請自行fill in your blank)。
在你拆開這些包裹之前,更迫切是要對自己(或preferably對宇宙)有一種「我搞得掂嘅!」的信任,否則面對一地有待解決、血肉模糊的真實面相,只有崩潰和崩潰。
對自己,我們都有盲點。可以是因為偏執,也可能是在生活太難過時讓自己好過一點的方法——對自己的「選擇性看見」。畢竟要正視自己的脆弱,比面對任何苦差都更難。
不是故意矇騙別人欺騙自己,而是,我們都總是看不見自己。
現代人,但凡要向外表達自己(social media & such),因多了「觀眾」這個環節,或多或少會自我美化。又或,因累積的讚美褒貶、曾經的被取笑、被吹捧或者被欺凌,而多少學懂自我保護,學會別把太真實的自己展露於人前。
但作為創作人,太顧及所謂形象(有偶包),未能在日常自省和創作中盡量接近最赤裸的誠實,也有礙成長。
兩週前看了杜Sir「嗰個」訪問,眾人焦點自然落在他的敢言,我倒是被他那份對自己赤誠的堅持,深深觸動。
一個人,站得越高,越難把自己的保護衣打開,坦蕩蕩地檢閱自己——自己和創作的關係、對家(香港)的迷思、對環境變更的不適應。
他說他不想走,但留在這裡其實又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慣於捉緊時代脈搏去說故事的人,在時代的脈絡亂掉時,不能,也不想,勉強自己做一些不誠實的作品。
在鏡頭前展露出如此的真實和謙卑,大師如他,要直接向觀眾承認自己的迷惘,沒幾個人能做到。
人們慣於好好隱藏自己的脆弱,絕大部分因不自信;怕一旦讓這個內在小孩袒露於人前,便從此被小看,無法站起來。
然而,創作人要寫出能真正觸動自己(觀眾會否被牽動已是後話)的作品,少不了這種血淋淋地掏心掏肺的過程。
敢於包容自己的脆弱,才是真正的強大。
他在訪問被問到:「你現在拍的是怎樣的題材?」
「我通常都講唔到㗎。我拍戲呢,係拍完先知自己做緊乜,拍之前係唔知㗎。」
這句話讓我想起許鞍華導演近作《詩》(紀錄片)裡,詩人飲江在訪問中提及他的作品《陰謀不沾染世界》。他說,這首詩的最後一句「親愛的,你就是那個可想」,在當刻寫的時候,其實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意思,到後來重看,才發現這句來得還真有意思。
「過程」,就是詩人和藝術家的目的地。
也想起David Bowie這個訪問。
“I think most artists feel a lot happier discussing the process of what they do, rather than what the hell it means. I know so many painters who title their work after they’ve done them. Which is a real giveaway.”
也不是不能先定主題再創作,但要捉住比我們mental ability更高層的體會,便要把注意力放在探索的過程中。
又,看了Joan Didion的 “A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
也是生勾勾血淋淋超honest work示範。
作家在一年間面對丈夫的離世、女兒躺在醫院和怪病搏鬥的現況,無助又無力。歷劫過後,唯一最靠得住的出口,就是寫作。
打開書的第一版,不由得dropped jaw。作家丈夫John Gregory Dunne離世的日子,剛好是2003年12月30日。
我師傅離開的同一天。
“The way I write is who I am, or have become, yet this is a case in which I wish I had instead of words and their rhythms a cutting room, equipped with an Avid, a digital editing system on which I could touch a key and collapse the sequence of time, show you simultaneously all the frames of memory that come to me now, let you pick the takes, the marginally different expressions, the variant readings of the same lines. This is a case in which I need more than words to find the meaning. This is a case in which I need whatever it is I think or believe to be penetrable, if only for myself.”
整本書,就是從這一天開始,一年間的哀悼日記。
“The only way out is through.”
在苦難中要超脫、要跨越,唯一的方法,就是正視傷痛、正視軟弱、正視自己一直避開不想看的傷痛和不安。
然後以最誠實的姿態,直闖,衝過去。
p.s. 這個關於“Honest work”的題材想寫一陣子,又有點猶疑。如今終於寫了,有點跳。或許也就秉承幾位大師所描述的「寫完先知自己想寫乜」,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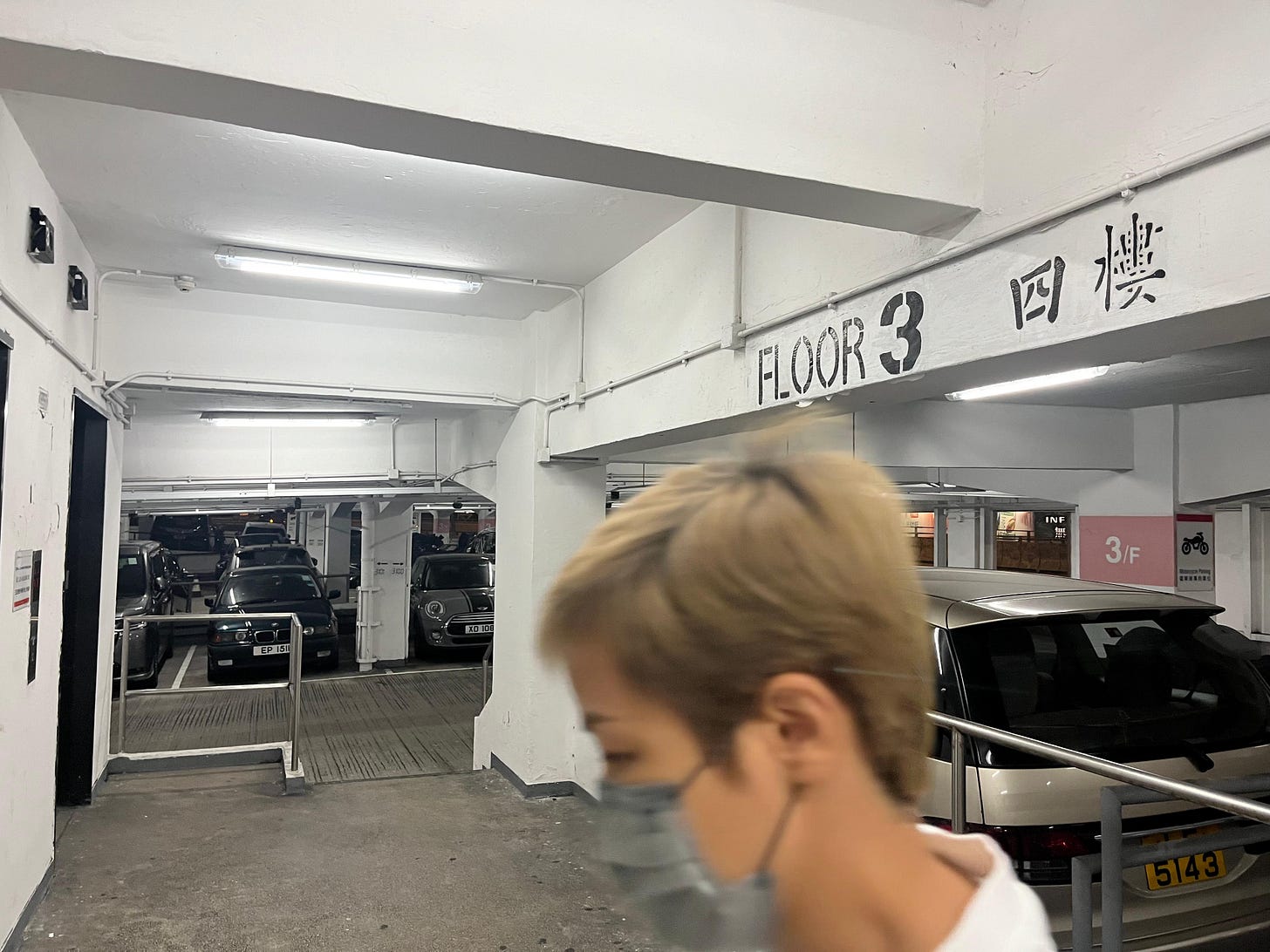
曾经有段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也没有力气去思考。很迷茫。后来发现是因为心里有很多伤痛和出脆弱无法直面。走出来过后发现诚实对待自己真的很重要。我想人并不是小时候说梦想那般决定自己是谁,做什么事。是一步步往前走,对自己诚实才知道,碰撞出自己的形象,才知道自己是谁。千与千寻里面汤婆婆说,曾经发生的事不会忘记,只是暂时记不起来了。对我,那些曾经刻意被自己放置一旁的,因为羞愧,害怕或者是其他负面情绪而不敢去看的自己,在诚实面前慢慢出来了,原来并不丑陋。真善美,一定是有真才可以去往善良和美丽。
诚实面对自己真的很难。
大概4年前开始写日记(当然忙或者懒时变成周记或者月记😅),我才发现原来没有“观众”的时候也不见得能诚实面对自己,好像原来心里那个“自己”才是真正的观众。
而且诚实也需要能力去分析,而不是被自己营造的表象骗到,更需要勇气面对与“人设”和自我想象中不一样的自己,有时候会感慨“啊,原来我是这样想的”,“原来这才是真实的我”。但这样的时刻越多,越觉得轻松,我想这就是接纳吧。